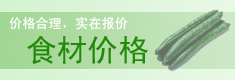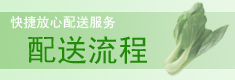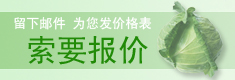“�˃r���ǝq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Ҳ�]��ٍ�c�X��”���죬���ڴ����Ъ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尙��ü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IJ˵؇@�˿ښ⡣
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␞���׃���r���A����꣬�r���Gꖸ��գ��@�ڰ��ƅ^(q��)�˺��(zh��n)�f����IJ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ܟ�������Ҋһ�����֞��Ɖ�픣�����æ��һ߅����ѝ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ѥ��һ߅ָ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“�@Щ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ˣ�”
����2007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һ�𱳾��x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ݴ�ƴ���]�đ{�]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y�ԾS��һ���Ŀڵ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ǣ�ݚ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ƅ^(q��)�˺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f���壬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N�Ϻ��ࡢ���ˡ�ͨ�˵������߮a(ch��n)���߲ˡ�
�����˃r�q���^�ɱ�“�˃r�q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ǧ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߲˸��NҎ(gu��)�ɵĄ��壬�ܿ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һ��ٍ���˵�һͰ��ƴ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ʮ�f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^��һ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þ����L��2008��V�����ܺ�Ҋ�ı���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w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꣬�]���u���]���룬��ĺ��y��”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з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ӻ��ϼ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D�y��2008�꣬�˃rҲ���ϝqڅ�ݣ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s�f���벢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Y���̱�Թ����“�˃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҂��ijɱ�Ҳ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MҲ��”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һ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ˎ�Ɏ���ǰ�Ď�ʮ�Kһ���q����200�K���˷N�Ƀ���ëһ���q���߰�ë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߰ٝq���˽�2000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r�ɴ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ꠛQ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f���پͶ��١�����߀�f���ټ��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࣬�@30���ؾ���9���ڷN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Ҳ�ͷN���Į��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ُ�̉��̓r��“���u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ˣ��߲˵���ُ�r�s�]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ӣ�“�F(xi��n)�ڵ��߲���ُ�r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u��ȥ�ăr��ܸ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”���ƅ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IJ��r(n��ng)�T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ͬ�ӵğ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e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ُ�r������ë�X��ͨ�^��ُ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ֵ��Ј������uһ�ɉK�X��
����ÿ���峿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T���嶼��(zh��n)�r���ȴ���ُ�́���ُǰһ���ո�õ��߲ˡ����ֻ�а���4���Ҏ(gu��)ģ���^С���T����]���I�߲��ո�C�����еIJ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̃ɂ�������砵�һ��һ���ո����ģ��@�ӵ��ո����ÿ�춼Ҫ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С�r���ո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؏�(f��)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ˮ��ʩ�ʵ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Ӱ푣��T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ُ�̑{�讔(d��ng)���յ����߲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ُ�r��“���ٲ˾��F���˶�˾��v��”�T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ُ���߲ˌ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ƅ^(q��)���·�A�ϵ^(q��)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Ј�——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Ј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؛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ӛ�ߣ���ʹ�߲˵��Ј��rҪ����ُ�r�߲�ֹһ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]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߲ˣ�Ҳ�]�r�g�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�u���ټ��ϵ��Ј��u��ÿ����Ҫ�Г�(d��n)��ǧ�K�ęn�����ɢ�u�װٽ��߲˲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x��ֱ���ˮ�(d��ng)?sh��)ذ��߲˵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o��ُ�̣�����ُ�r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ُ���f���㡣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ܟo�Σ�“��ُ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X�Ͷ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u��Ԓ���װٽ�˾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ݵ͜ض�����씵(sh��)�^����࣬��(d��o)�V�ݵIJ˃r“�Ӹ��y��”���Ј���5�K���µIJ˲����࣬���ĵă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10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i��ăr���ஔ(d��ng)���߲˵���ُ�r�ձ�����˃���ë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ԣ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벢�]�кܴ�ĸ��ơ��Y���̱�ʾ����ⲻ�ã���(d��o)�²˵��ճ�Ҳ�٣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Ҳ�]�˿��u��
�����]�a�N���L(f��ng)�U������“�N�˱ȿ�С��߀ҪС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h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أ�һ߅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ⱻ�����ĵı�Ĥ��һ߅Ĩ��Ę�ϵIJ�֪����ˮ߀�Ǻ�ˮ��ˮ�顣
����“�V�ݵ����׃�þ��ǿ죬�҂��IJ˲���̫��̫�ᣬҲ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ı����С��߀ҪС�ģ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鲻�Ǵ�Ҏ(gu��)ģ�Ĺ��߷Nֲ����ʹ�߲��ճɲ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⌧(d��o)���w���o�գ�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Լ��Г�(d��n)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߲��a�N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ț]�ճɸ����µ��ǜ��N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2011���ձ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ĺ�й©�¹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ݗ�䣬���ҳԣ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N�IJˠ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“�]�a�N���҂�Ҳ�]�k����”��һ�꣬��̝�˃����fԪ��
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@Щ�ڏV�ݽ����N�˵��r(n��ng)��ց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ؽ�(j��ng)�I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N�Ϻ��ࡢ���˵��N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ߵ�Ʒ�N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ϲ�g�N���ĵȃr�����F��Ʒ�N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Ҫ���N���ճɕr�g�L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ֻҪ�Բ��磬�ճɿ졣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r�£��@Щ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ˮ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]�ˇLԇ�W(w��ng)��ֱ�N��Ҳ�]�����^�M��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һ�N�ۣ�ֱ���u�o���С��?zh��)õȣ�ֻ�����ό����N�ˣ�Ȼ���u�o��ُ�̡���֮��СҎ(gu��)ģ���ָ��N���I����Cе��Ч�ʵͣ��ɱ�Ҳ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̫���ˡ�
�D��ժ�ԾW(w��ng)�j(l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֙�(qu��n)��Ո(li��n)ϵ�h��